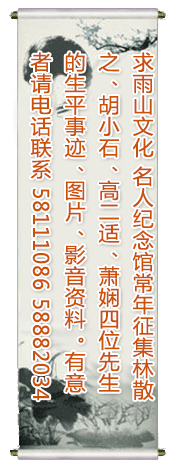論高二適的手札書風
金 丹
內容提要:本文從手札書風的角度出發(fā),探討高二適的書法藝術,指出手札書風是高二適書法創(chuàng)作的一大亮點,極具個人風格特色。同時對其書法觀及其在書法史上的貢獻進行闡述,認為高二適的草書在碑派馀緒籠罩的現(xiàn)代書壇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高二適 手札 草書 書風
一、草圣平生:高二適其人其書
提起高二適,人們都知道六十年代的那場“蘭亭論辨”,名聞遐邇。如果撇開“論辯”,單就高二適的草書藝術成就來說,也足以載入史冊,與歷史上的草書大家共同演繹一部精彩的草書藝術史。
高二適(1903—1977),原名錫璜,號舒鳧、舒父、瘖庵、麻鐵道人、秦老詩逋等。江蘇東臺人。16歲考入揚州師范學校,后因家貧輟學。遂在鄉(xiāng)里教學,并子承父業(yè),18歲時接替父親任立達小學校長。25歲考入上海正風文科學院,次年考入北平研究院國學研究門研究生。曾于假日游學京滬,先后師從戈公振、韓國鈞、章士釗先生。60歲時經(jīng)章士釗引薦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1】《劉賓客文集校錄》。
高二適對自己的草書十分自負,他自許“草圣平生”,自謂“世人無我,我無世人”、“二適,右軍以后一人而已,右軍以前無二適,右軍以后乃有二適,固皆得其所也。”【2】以至有不少人謂其狂妄。林散之在詩中這樣表達他對高二適為人的看法:“人皆謂之狂,我獨愛其直。”【3】
高二適在楷、隸、行、草書方面都下過功夫,尤以草書著稱于世,并以雜體草書獨立于晚近書林。他有學書自述:“余不敏,幼承先人余業(yè),篤嗜臨池,然草書無法,中心疚之。不得已,乃日取唐本《十七帖》、《澄清堂帖》、《淳化閣帖》及《淳熙秘閣續(xù)帖》諸本,專攻王羲之,習之既久,遂得稍悟真草之書,非由草、隸、篆入門,不能得其正軌焉。”【4】從選帖來看,可見他對草書的偏愛。當然他臨《西狹頌》、《楊淮表記》等隸書,臨《賀捷表》、《七姬帖》等楷書,以及臨《圣教序》、《大唐紀功頌碑》等行書,對他日后書風的形成起這重要作用。50歲以后的高二適專攻章草,致力于《急就章》的研究,同時朝夕臨摹皇象和宋克的作品,他說:“歲次甲午,余年逾五十矣,乃出舊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暨元人宋克補本,朝夕臨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則,乃由篆隸省變?yōu)椴葜緩健!薄?】他尤喜臨宋克,這對于他雜體草書書風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的草書觀是“學草要兼章”,也就是在學今草之外要兼習章草。他對書法史上的張芝、索靖、羊欣、薄紹四位擅長章草的書家頗位推崇。有“骨節(jié)張索”、“江東羊薄”二印表明了他的觀點,見載于鄭逸梅《藝林散葉續(xù)編》。他還對人們對章草大家皇象的淡忘表示出不滿:“漫天惡札世爭奇,皇象工書人不知”。他批評宋人草書說:“宋人筆法無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規(guī)范,故致此耳。”又認為:“若草法從章法來,則高古無失筆矣”。在高二適看來,草書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能發(fā)泄吾人胸中之馀蘊,如心有悲愁抑郁,起而作草最為能解也。又,凡人有抑郁不平之氣,作草亦可解也。”高二適的這一見解,在他的草書作品中最能反應出來。
二、金薤琳瑯:高二適手札書風及其特色
在高二適的書法作品中,草書是其成就最高者,而在他的草書作品中,手札書法是其一個亮點,也成為高二適書法的一個重要特征。
手札,古人又稱尺牘、尺素、尺翰,因其書函長約一尺,故有此稱。尺牘一詞見于《漢書》,其《陳遵傳》云:“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孫過庭《書譜》云:“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后答之,甚以為恨!”王獻之因為謝安沒有收藏他的手札而甚以為恨,說明手札在當時已成為書法欣賞的重要組成部分。晉人書法賴以手札而傳世,陸機的《平復帖》成為書法史上最早的名人墨跡,這是書法史的一種獨特現(xiàn)象。二王手札,是有意無意間的書法杰作,說無意,它是一種輕松自然的流露,沒有束縛;說有意,它又不可能完全是為了寫信而寫信,字里行間是一種書法技巧和才情的表現(xiàn)。二王手札已成為千百年來人們學習書法的經(jīng)典,孕育過無數(shù)帖學書家。隨著時代的變遷,書法的樣式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明清兩代更是以條幅巨制見長。晚近書壇受清代思潮的影響,也呈現(xiàn)出厚重的氣象。高二適不然,他的書法作品雖有大字和巨幅,但手札書風已經(jīng)成為他書法的一個形象,一個特色,在現(xiàn)代書壇顯出特別的與眾不同。
高二適的書法作品也是形式多樣的,有條幅、對聯(lián)、橫幅、中堂、扇面、長卷等,由于他對自己的書法作品比較謹慎,加上他不輕易給人,自視“一字千金,不啻小王之作草也”,【6】所以作品傳世并不多,但是在有意無意之間,給人們留下了很多手札、詩稿等。如《高二適書法選集》、【7】《二十世紀書法經(jīng)典——高二適》、【8】《費在山藏現(xiàn)當代書畫墨跡選——高二適卷》【9】中收錄的作品,手札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另有《高二適手札》出版。【10】這些手札作品多是給老師、友人的書信,卻流露了他的心性,似乎讓人領略到他的內心世界。高二適認為:“草書即須乘興而發(fā),始能為之,此草書不二法門。”【11】而他的草書手札正是乘興、即興之作,尤能發(fā)其胸臆,形其哀樂,見其情性。他的手札作品已經(jīng)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了,時而興之所至,洋洋灑灑,能將手札寫成橫幅,乃至寫成手卷,大大突破了尺牘的范圍,這也成為他書法作品中的一種獨特的表現(xiàn)形式。
在高二適的手札中,《致章士釗先生》數(shù)札、《致卞孝萱先生》九札和《致費在山先生》數(shù)札都是高二適手札中的精品。他一生致人手札較多,如致蘇淵雷、亞明、丁吉甫、蕭平、徐純原、張爾賓、莊熙祖、桑作楷、劉墨邨、薛文浩、高景云、方志鎧、李春坪、謝居三、王思任等,其中也不乏精品。
當然還包括一些詩稿和題跋,如高二適1973年《呈散之先生詩稿》、1974年《贈繼海詩》、1975年《致陶白詩稿》、《贈純原詩二首》、《答蔣永義書兼眎阿松》,以詩代訊,也可以看作是手札的一種。在詩稿和手札之間的這類作品,也是詩人兼書家高二適的一大特色。風格也趨于統(tǒng)一,我不妨統(tǒng)稱為“手札書風”。
用沙孟海題《二適詩信墨跡冊》中的“金薤琳瑯”四個字來形容他手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感受是很確切的。在高二適的手札中,以草書為主,雜以隸、楷、行書,可稱為雜體草書。他自己曾說:“余作草以章草、八分、行書相間為之,此王右軍法也。”【12】此法元人趙孟頫、康里巎巎、饒介已經(jīng)涉及,實際上到了明初宋克將這種雜體草書寫出了一種鮮明的風格,高二適也承認:“四體書,宋仲溫始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此俟知之者。”【13】正因為他的雜體草書,使得他的草書有“金薤琳瑯”般的華麗和變化之感。
綜觀高二適的手札作品,從對象上看,有致老師、同門、朋友、學生的。從內容上看,談學術、談書法、談雜事,也有談詩和以詩代訊的,均有感而發(fā),常常流露出他的學術思想。從書體上看,以草書為主,間以楷、隸、行,并很自然地糅合在一幅作品上。高二適稱之為“四體書”,于右任稱宋克的這種書為“混合體”【14】,此處不妨稱為“雜體草書”。從形式上看,有信箋、詩箋者,但他并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實際上已經(jīng)在“尺牘”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拓展,小的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般小條,大的如橫幅、手卷式的手札。從手札作品本體來看,隨著情緒的節(jié)奏,時而快速書寫,幾個草字連在一起,時而放慢速度,在草書中出現(xiàn)一兩個楷、行書,顯出節(jié)奏感。時而因為注釋或缺漏,或在信寫成后想到要特別補充的,在正文中和文末添加小字,顯出豐富感。與小字相比,有時一字之豎能一瀉千里,如《致卞孝萱先生札》中有一“耶”字竟有15字之長,甚為過癮【15】。出于禮貌,時而抬頭,時而空格,因為錄詩,有意與信有所區(qū)別,故手札的整體高低錯落,疏密有致。時而圈劃和涂改,時而以朱砂或墨筆圈圈點點,作些句讀,當然這一切都是順其自然的,也是古人手札和文稿的常見手法。從用印上看,多數(shù)手札鈐印,有興致時可鈐多方,有名印,字號印、引首印和閑章,所鈐位置也很自由,并不刻板和拘泥程式。有印章蓋倒和蓋歪者,也有未鈐印者,可能由于當時的種種原因所致。“二適頓首”、“二適拜呈”、“二適叩復”、“二適謹狀”、“二適便書”、“二適手寫”、“二適具草”將我們帶到他作書時的情境中去。我們讀這些手札,感受頗深,這是思想、學養(yǎng)、生活、情性、技巧的高度統(tǒng)一。
他的手札,有氣勢,寫得大氣磅礴,有江河奔流之勢。他的手札,是生活,寫得情感流露,不避忌諱敢于慷慨直言。他的手札,見情性,寫得隨性所發(fā),不拘小節(jié),而神態(tài)自若。他的手札,顯爽健,寫得沉著痛快,抑揚頓挫中見連綿起伏。他的手札,能疾澀,寫得緩急互見,盡書道之妙。他的手札,寓高古,寫得兀傲不群,頗有犖確不平之氣,更見晉賢蕭散之風。
1977年3月15日,揚州書家魏之禎在讀了方延午所集《舒父老人手札冊》后,成詩一律:“常侍詩篇富,伯英草法嫻。情懷哀樂外,根柢有無間。尺素玲如璧,錦裝駁且斑。望崇擬往哲,師傅老虞山。”【16】對他的尺素之作表示出由衷的贊嘆,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三、風流獨步:高二適手札書風及其草書的歷史價值
高二適手札書風的形成,有兩點最為重要,一是與他長期臨習《十七帖》、《淳化閣帖》這樣的先賢手札不無關系。在十年文革中,他仍在臨習二王手札,他在《淳化閣帖》卷七中題道:“六六文運,僅存此冊,夜便狂書十紙。不死適老子題。”【17】二是與他所處的時代和環(huán)境密不可分,他需要寫信,也樂意以寫信來抒發(fā)情感,向人傾訴他的內心世界。因而他有大量的手札存世,足以使得在他的書法作品中,手札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形式,成為他書法的主要特色。
林散之在看了摯友高二適的遺墨后,有詩:“矯矯不群,坎坎大樹。嶷嶷菁菁,左右瞻顧。亦古亦今,前賢之路。不負千秋,風流獨步。”【18】
高二適的手札以草書為多,而草書得益于章草尤多,當代草書家從章草中走出的,我認為有兩人風格迥異,并形成自己鮮明藝術風格的,一位是王蘧常,一位是高二適。王蘧常以碑法寫草,遲澀凝重;高二適以帖法寫草,爽健飄逸。前者在清代碑學書風的馀緒之下,順應了歷史潮流,應屬理直氣壯。后者頂著碑學的籠罩,恢復古人帖學傳統(tǒng),與時人的書風拉開了很大距離,實屬難能可貴。相比之下,高二適更具有歷史意義。
高二適草書風格的形成,與他的書法觀有著很大關系,是他書法思想的直接映現(xiàn)。首先是他不隨波逐流的思想。他說:“吾素不樂隨人俯仰作計”,這是他在“蘭亭論辯”中表現(xiàn)出來的。其次是他崇尚帖學而鄙視碑學的書法觀。他對二王一系帖學經(jīng)典的崇尚在各種手札和題跋中可以讀到,如“吾嘗謂中國書史中有三大寶物,即史遷之文、右軍之書、杜陵之詩是也。”、“平生只嗜晉帖,晉帖以后,只一五代楊風子、康里子山及宋仲溫二人,此非十駕之功不可追也。”他對碑學的鄙視,從他在碑帖上只言片語的題跋上也能讀出一些端倪來:他論包世臣:“其人于書無妙解”。他論康有為:“惡札可憎”。他論沈曾植:“字形拙劣,沈君枉有書名,現(xiàn)世無具眼久矣。”快人快語,愛憎分明,表明了他崇帖貶碑的書學立場。再次是他獨立的人格精神的反映,他的草書風格與他的性情完全吻合。
高二適的書法貢獻有三。一是頂著碑學風氣,堅持帖學創(chuàng)作,使得帖學有了發(fā)展的空間。他崇尚帖學,對清代以來的碑學有著強烈的不滿。六十年代的那場“蘭亭論辨”應該視為他對碑學的一次公開反叛,這是一次碑學籠罩下的帖學覺醒。如果說“蘭亭論辨”表明了他崇尚帖學的鮮明立場,那么,他的書法則向人們展示了他對千年帖學的傳承和發(fā)展的風采。高二適在《致費在山信札》中曾透露沈尹默對他書法的看法:“吾在蜀作唐人帖,吳興沈下翁(沈尹默)見訝,告章行老,稱三百年來無此筆法。解放后,予在滬屢與秋明(沈尹默)晤談(當時潘伯鷹尚健在),事隔二十馀歲,伯鷹仍牽此陳事為笑樂。”【19】可見以振興帖學為己任的沈尹默對高二適書法的地位看得很清楚。
二是高二適專攻章草,使得沉寂已久的書體得到發(fā)展,并運用雜體草書,使得他的書法風格與時人拉開距離。對于章草,他認為:“章法墜失已有一千六百馀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滅。”他對于章草的整理研究和書法實踐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又說:“書既蕆事,輒用真行草書四體書之,并親用竹木簡之筆法,籍證我國文字書史,自漢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殘守缺之舊觀,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異之局勢。”【20】可見他在尋求古人的筆法,來創(chuàng)造自己的書風。他在《致?lián)P州方延午先生手札》中說:“鄙心率不齊病,仍未痊愈,惟近忽有意創(chuàng)一書體。”他欲創(chuàng)一書體,就是指他的這種“雜體草書”,而“雜體草書”并非他所發(fā)明,他所說的創(chuàng),應該是指具有他自我特色的風格意義上的書體,也就是高氏雜體草書。這說明他有意于書法的創(chuàng)新,而他走的也正是前人的“入古出新”之路。
三是手札書風在近現(xiàn)代書法創(chuàng)作樣式及其情感表達中的作用。近現(xiàn)代書壇是晚清碑學的延續(xù),雖有沈尹默、白蕉等致力帖學的倡導和創(chuàng)作,但人們的書學思想仍然在碑學的思維模式之下。從作品樣式來看,以條幅、屏條、中堂、對聯(lián)、扇面等為主要創(chuàng)作模式,展覽的頻繁,更使得尺幅越來越大,手札這樣的形式在晚近書法創(chuàng)作中漸漸淡出書法舞臺。實際上,手札這樣的展示形式是帖學的淵源,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高二適的書札書風給人們帶來一陣清新之風,將古老的帖學以新的面貌展示在人們面前,給書法創(chuàng)作樣式以新的啟示。此外,手札書風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還不只是樣式,更重要的是手札表現(xiàn)出來的是真情實感,反映了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高二適在一封手札中說:“凡人有作,須有所寄托,不然,則字匠之為,有識者定嗤之以鼻也。”【21】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創(chuàng)作更接近于書法的情感表達。
當代的書法展覽中也有一些手札式作品,故意抄錯唐詩宋詞,涂涂改改、圈圈點點,也有故意寫信,無病呻吟,造作之極,反映的是假生活、假情感,不能與高二適的手札書法相提并論。“手札時代”已經(jīng)成為過去,高二適的手札書風帶給我們的啟示,不是讓我們去模仿,而是通過這種現(xiàn)象,能夠啟發(fā)我們的思維,對當代的書法創(chuàng)作提供一種新的空間和可能,在讓我們的書法創(chuàng)作怎樣更加貼近真實的生活狀態(tài)上作一些有益的思考。
注釋:
【1】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高二適《題澄清堂法帖》,見《高二適研究》P34,《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
【3】林散之《春日寄懷二適》,《江上詩存》卷二十五,P238,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
【4】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證》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證》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6】高二適《致丁吉甫手札》,見《高二適研究》P37,《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
【7】《高二適書法選集》,江蘇美術出版社1987年。
【8】《二十世紀書法經(jīng)典——高二適》,廣東教育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
【9】《費在山藏現(xiàn)當代書畫墨跡選——高二適卷》,香港王朝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
【10】《高二適手札》,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2年。
【11】高二適《跋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見《高二適研究》P33,《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
【12】高二適《題墨池編》,見《高二適研究》P30,《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
【13】高二適《題宋克書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見《高二適研究》P30,《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
【14】于右任《跋宋克書杜甫壯游詩卷》:“故此種草,謂之為古今草書中之混合體則可,如謂為章草,則誤矣。”見《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法書九》P71,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委會1986年。
【15】高二適《致卞孝萱手札》九札之一,冬青書屋藏。
【16】魏之禎《題舒鳧墨跡》,見《高二適研究》P96,《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
【17】轉引自尹樹人《高二適書法選集序》,見《高二適書法選集》P3,江蘇美術出版社1987年。
【18】林散之《題摯友高二適遺墨》,見《高二適研究》P95,《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
【19】從高二適《致費在山手札》原跡中錄出。
【20】高二適《新定急就章及考證》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高二適《致徐純原手札》,見《高二適書法選集》P75,江蘇美術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