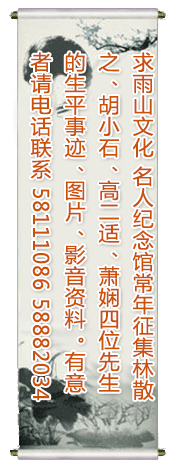從古代書法史上之“正統觀”看當代書法核心價值的建構
李慧斌
【提 要】本文以史學上之“正統論”為借鑒,比較深入地考察了中國古代書法史上的“正統觀”及其具體表現。提出了“書統”與“道統”一體的觀點。并以史為鑒,對當代書法核心價值的建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書法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要能夠在當代文化的復興運動中有所擔當,而作為當代人的我們更要義不容辭地擔當起書法藝術在我們這一代怎么樣傳承與發展的重任,從而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高潮推波助瀾。
【關鍵詞】古代書法史 正統觀 當代書法核心價值 文化
正統觀念是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問題,“正統論既是中國古人的一種歷史觀,又是史學活動的修史依據,是對政權叢生、錯綜復雜的王朝興衰的一種判斷和看法,也是修史時對紛亂如麻的歷史線索的一種梳理和描述。正統理論既是史學家在處理歷史問題時所形成的觀念和理論,反過來又對現實政治和未來歷史產生深刻而深遠的影響”,“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此正可窺見中國史學精神之所在”。[1]史學上存在著“正統論”的觀念,那么在古代書法史上是否也存在著“正統觀”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是否可以通過對書法史上“正統觀”的考察,對當代的書法發展尤其是書法核心價值的建構提供一定的借鑒呢?答案也是肯定的。這正是本文寫作的初衷。
一 古代書法史上“正統觀”的表現
“正統觀”是書法傳統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和組成部分。在古代書法史上,正統觀的相關內容在書論文獻中有很多記載。但總結起來不外兩種類型:一是書法在服務于帝王政治統治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正統觀”——道統,它是文字——書法的社會教化功能的集中體現;二是書法作為藝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正統觀”——書統,它是書法文化屬性與人文精神的一種體現。宏觀來看,“書統”也要服務于“道統”。
書法“正統觀”的形成和中國古代帝王的政治統治密不可分。古代書法史有著一種很特別的發展現象,那就是自漢魏晉書法藝術“自覺”以來,書法的發展便一直與帝王政治相關聯,即書法與政治統治具有“一體性”的特征,這就決定了書法史上存在著“正統觀”,而這又成為了統治者的一種“治具”,所以歷代統治者都要加以重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書法的社會實用屬性——“記言紀事”功能——文書一體的特性,即由作為歷朝歷代正體文字書寫而附帶的正體書法的發展與正統觀的形成。其理論依據主要有三:一是許慎《說文解字?敘》所云:“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2]二為張懷瓘《文字論》所說的:“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為用,相須而成……紀綱人倫,顯明君父……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3]三是項穆《書法雅言?書統》所論:“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圣賢之學術,至于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為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圣道也。”[4]當正體書法一旦承載著“經義之本,王政之始”、“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正書法之所以正人心”的歷史重擔時,書法就已經不僅僅是作為游藝欣賞的藝術了,而是成為帝王政治的一部分,被納入到了“正統”的序列。誠如宋徽宗所認為的,“書之用于世”的目的,就是要“一道德,謹守法,一同天下之習”,最終達到“書同文”的政治教化目的。書法在服務于統治過程中形成的“正統觀”,說明了歷代帝王對書法的重視,書雖“小技”,卻可通“大道”。
另一方面是由書法本身的藝術性引申、附帶出來的政治成分而形成的“正統觀”。可以說書法的藝術魅力在政治意志之外征服了帝王,帝王好而用之,投身其中。從漢代“善史書”風氣中帝王的參與,到魏晉南朝帝王書法實踐的投入與風尚的形成,再到唐宋以來形成的“宸翰”在書法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無不說明帝王已經成為了古代書法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以其獨特的身份在書法史上發揮著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書法風尚和觀念的形成。當唐太宗專門為王羲之寫《傳論》而崇王時,《宣和書譜》的著述者認為李世民此舉有借書法“粉飾治具”的意圖。這一針見血地指明了書法除了其實用性即正體價值外,書法的藝術性也是可以納入到帝王政治統治的“治具”當中,只是這一方式比較隱晦罷了。但無論是哪一方面,當書法一旦成為了一種“治具”,便自然載承著特殊的歷史使命和一定的政治意義,“正統觀”也藉此得以形成。
書法作為藝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正統觀”——書統,有幾個方面的重要表現。其一是唐代以來王書大統的確立,以及宋以后顏書體系的建立,王、顏二系遂成為古代書法史上的統序。從唐太宗尊王,用“盡善盡美”的儒家審美標準把王羲之推上了書法大統的地位,再到項穆崇王,稱“宰我稱仲尼賢于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鐘、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項氏把王羲之和孔子相提并論,這正說明了王羲之書法正統觀的確立要能符合儒家的道統觀。另外王書大統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從宋代開始明確了以顏體為代表的唐宋人分支線索,與王系并行,而統歸于王。所謂顏書如同杜詩,“一出之后,前人皆廢”。[5]顏真卿能成為“書之大雅”,關鍵在于顏真卿的人。金人元好問就曾說:“予嘗觀顏魯公帖,可想見其氣節,可發人理義之心,有道德之味存焉。”[6]元人王惲在《顏魯公書譜序》中對這種“教化”意義說得更直接、明確:“今觀魯公之書,可以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于風教者乎?”[7]如此,顏真卿的書法已經不僅僅是藝術了,而是被納入到了正統行列,成為了教化的一種特殊形式。這正如《衍極》所云:“顏真卿含弘光大,為書統宗,其氣象足以儀表衰俗”。[8]從書法理論的角度來看,王系與顏系正好可以互配、互補。如果說王書以行草為主代表的是魏晉風度,有著道家自然精神和儒家“盡善盡美”的審美追求而更趨于藝術的話,那么顏書以實用楷書為主代表的是盛唐氣象,有著儒家積極進取的士大夫精神而更近于現實,標準便是“含弘光大”。顏書與王書相配,正能滿足讀書人、文人、士大夫們對于文字書寫的現實與藝術的雙重需要。
其二是筆法傳授譜系中的正統觀,并由之引申出“古法”與“趨時書風”的問題。古代的書法教育和學習主要有“師范”和“家承”兩種形式。在古人看來,書法學習一定要師出正脈,有統有序有淵源。所以,在這樣一種正統觀的影響下,古代以名家傳授筆法的譜系才得以形成。關于筆法傳授譜系的考論,已有諸多可參考的研究成果,[9]但需要補充的一點是,筆法傳授譜系的形成,很有可能是受了儒家道統觀念傳承的影響,饒宗頤先生認為:“自韓愈《原道》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再傳至湯、文武、周公、孔、孟,儒家道統承傳之說于焉確立。”[10]孔孟儒家學說的最終確立,就像書法領域王顏二系的建立,終成大統。所以書法史的發展若以書家為主線的話,大都是要圍繞著這一筆法傳授譜系進行選擇。守法度者以其取法正宗而得“嫡傳”之名,出新意者以其不離正軌而得“創變”之意,卻仍歸譜系之中。此猶如鐘擺,以中時為正統,以側擺為變數,但終歸要回到正統之位。對筆法傳授譜系的尊崇,還影響到了“古法”與“趨時書風”的討論。毋庸置疑,學古法是正統,而學時人之書當為末流。對此,米芾就曾對宋代的“趨時貴書”進行過批評,認為這帶來的最大危害就是“自此古法不講”。[11]不講古法,書法的統序就要出亂。明代豐坊在《書訣》中也曾批評過“永、宣之后”的趨時書風,造成的結果是“古法無馀,濁俗滿紙”,[12]無有師法,不得雅正之旨。所以,學古法才是書之正統。
三是書法批評上的正統觀——書如其人的理論建構與文人士大夫書法的正統地位。“綜觀古人論書,以人品推及書品者,其思想宗旨仍在于如何按照既定的標準來作人。郝經《移諸生論書法書》‘蓋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之論,可為其總括。如果究其社會的與文化的深層涵義,則可歸結到儒家的倫理秩序,是把封建社會用以教化人的倫理道德標準,轉化而為書法的評論、取舍標準”,“這是后期書法理論史的核心內容,也是影響書法審美與批評質量的一個敏感話題。”[13]后來,劉熙載的《書概》為“書如其人”理論作了最好的總結,云:“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14]書如其人觀念的理論化,使得傳統書法批評回歸到了儒家正統觀念上來。因此,書法借文化之力,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被追加和層累,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場”。而且這種“場”,從宋代開始,又確立起了以士大夫賢者為參照的書家取舍與評價標準,從而把那些以書法為事業者及書法伎術官們排除在這一評價體系之外,最終形成了書法批評領域中的“正統觀”。
此外,若就書史文獻的體例而言,也存在著正統觀。形式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歷代編撰書法史者多把帝王列在首位,以顯其正統及至高無上的地位。王僧虔《論書》就把宋文帝放在了第一位。在唐代,突出帝王在書法史上地位的意圖愈加明顯,尤其以張懷瓘《書斷》為典型。《書斷》卷中“神品”前的一段論述文字,就是要為帝王善書者立傳,并形成了尊帝王的觀念。到了宋代,帝王在書史文獻中的地位更是得到了彰顯,正統觀得以完全確立。朱長文《續書斷》專門在篇首列《宸翰述》一章,為宋代帝王善書者鼓吹。作為官修書史文獻的《宣和書譜》更是在卷首列“歷代諸帝王書(皇后附)”,足以說明帝王在書史上的正統地位。及至岳珂《寶真齋法書贊》、董史《皇宋書錄》亦皆專門于篇首列宋代帝王之善書者。這樣的一種觀念一直延續到明清。陶宗儀的《書史會要》也是在所分各個朝代的最前面首列帝王善書者,非但如此,還把“三皇五帝、三代列國”納入到了書法史統序之中,這更是古人追古溯源思想觀念的一種直觀反映。后來朱謀垔的《續書史會要》,作為明代書家的斷代史,于卷首也先列舉明代帝王善書者。最后是清末李放編著的《皇清書史》,在體例上也是受此種觀念的影響,于卷首專列“圣制(王公宗室附)”一節,以顯現清代帝王的書法成就。
如此,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之“正統觀”,以其與帝王政治統治的一體性而具有了與“道統”共存的性質,在作為士大夫游藝之“正統”和作為國家統治的“道統”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換句話說,書法一直是兼顧著藝術的“正統”和帝制“道統”的雙重屬性,對于書家而言又多是在技與道之間進行調和,最終體現“技道兩進”與“中和”的審美理想。
二 “正統觀”對當代書法核心價值建構的意義
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為當下提供啟示,也就是“以史為鑒”的觀念。所以,我們對古代書法史上“正統觀”進行考察的一個重要目的,也是要為當代書法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尤其是對當代書法核心價值的建構提供參考。
現實來看,盡管古代書法發展所賴以生存的各種環境在今天大都不復存在,但中國文化的血脈還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還在,中國人還在,中國的漢字還在,毛筆還在……所以書法的發展就應該在當代新環境下,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和突破,從而確立當代書法發展的正統觀,體現書法的核心價值。
書法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它必須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文化層面來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價值觀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價值觀”;二是以“大力推進和諧文化建設,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為主旨的“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由此看來,當代書法的核心價值就是要以國家民族的價值觀為核心,以書法所固有的獨特文化符號和藝術形式展示出中國文化傳統精華和內涵,以其獨有的、強大的生命力和社會影響,不遺余力地凝聚和傳播著中國文化傳統,并在當代承載著前所未有的人文情懷和時代精神。
從古代書法史上正統觀的具體表現來看,很多內容在當代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金開誠就認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歷程,不僅突出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智慧、想象力和創造精神,而且在藝術領域形成了它獨特的觀念和傳統。”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藝術只有有了傳統,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傳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是人類過去所創造的種種制度、信仰、價值和行為方式等構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與代之間,一個歷史階段與另一個歷史階段之間,保持了某種連續性和同一性,構成了一個社會創造與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密碼,并給人類生活帶來秩序和意義。”[15]惟其如此,中國書法才能憑借其傳統的生命力在當代得到更好的發展,才更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在正統觀的影響下,當代書法核心價值的建構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國家有關文化藝術的態度和政策導向。只有文化藝術的發展被納入到了國家高度的時候,才能結出碩果。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指明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就是要以“文化立國”、“文化強國”,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藝術的基礎上使得當代的文化藝術大發展大繁榮。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書法作為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形式之一,也應該承擔重要的使命。李長春曾說:“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為書法的發展提供了最好的時機。廣大書法工作者要抓住機遇,努力奮斗,繼續大力推動書法藝術的繁榮發展”。[16]這就是方向和動力。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和自強,首先取決于中國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個性和文化精神,這一點至關重要。熊秉明說“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在中國所有的藝術形式中,沒有那一種藝術能夠比得上書法這么接近中國文化的本質。在當代,書法的文化屬性必須得到加強。書法是以漢字為載體的文化性藝術,它的藝術表現形式、審美標準都是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書法藝術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而形成的一門獨特藝術,是民族文化、民族氣質、民族精神所顯現的文化符號。不能簡單地把書法看作是一門純粹的藝術形式,更不能把它看成是純粹的視覺藝術,否則,書法會失去它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性,如此也就會失去它的世界性。
2、中國書協作為當代中國書法發展的代表和主導,更需要有傳統意識,從學術到展覽,從回歸傳統到學養的提高,從書法教育到書法普及,從書法“大家”“名家”的推陳到“中青年提名”的出新等方面,都要樹立正統觀。在“中國書協關于書法現狀的座談會”上,陳洪武說:“中國書法家協會要引導廣大的書法家將書法創作向著健康繁榮的方向發展,把握好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努力為黨的文化事業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祖國的繁榮強盛服務”。[17]這說明,中國書協也是在為當代書法核心價值的建構而努力。無論是“經典意識”、書法“大家”“名家”的提出,還是強調展覽中作品的“原創”性、書家的修養、書法教育的普及等,都表明中國書協在當代書法發展中是積極的、大有作為的。歷史地看,經典意識是形成書法傳統的重要內容,而當代強化“正統觀”和“經典意識”就是要回歸傳統,回歸二王,回到雅正的書風上來。書法“大家”“名家”的提出更是書協有意要確立當代的書法楷模,為書法發展樹立典范。而“原創性”更是對書法學古的肯定和提倡,只有在傳統基礎上的臨古學古,才能在長期的書法實踐中形成自己的風格,而不是過早地“造”出風格。在書法文化精神構建方面,當代重新“發現”顏真卿,仍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書法批評傳統的回歸。當代書法的發展不缺少“創作”,而是缺少有效的“批評”,尤其是傳統意義上書法批評。在書法越來越過多地追求純粹的藝術形式的時候,書家離傳統的書法批評也越來越遠。所以當代書法批評的傳統文化屬性也在逐漸缺失。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書如其人”的批評幾乎成了空談。當代書家作為“文化人”多缺少“學養”,有的甚至缺少“德行”,所以才提倡“德藝雙馨”。歷史地看,強調人品學養對于書家是非常必要的。黃庭堅就說“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項穆也說“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這樣一來,修心養德就顯得格外重要。所以說當代的書法批評仍要秉承這一傳統,但要根據新的時代特點發揮其對書法家、社會、書法作品流傳、書法作品內涵的引導作用。在豐厚書法道德內涵時,要以強烈而光輝的人格為基礎,以美為標準。一方面要強調書法的倫理價值有助于提升書法家的品行節操,發揮社會功用;另一方面,書法倫理價值的凸顯不僅有助于書法作品的認可與流傳,還可以充實、豐富書法藝術的內涵,進而使其在歷史的維度中找到傳統的精神和價值。
在當代,應該說沒有那一種文化形式能夠比得上書法具有傳承接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條件。所以在看到這一點的同時,要確立起書法全面發展的信心。隨著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書法藝術更應該有它自己角色和責任擔當。書法作為國人進行倫理教化和精神陶冶的重要文化載體,能夠擔負起新時期的民族文化建設使命。同時,把書法作為本民族最優秀、最核心的重要文化資源,來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和對話,才能提升民族文化軟實力。書法的這種雙重功能不但保證了書法發展和民族文化發展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同時,更因其在發展過程中和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交融而成為民族文化的最好體現。
結 語
歷史地和現實地看,在近現代中西方文化碰撞與交流的過程中,中國固有的很多文化藝術形式都發生了質變,唯獨書法等幾種形式依然保持著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特性,不但沒有中斷,反而一直發展到今天。再有,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教育形態是以西方為參照的,當在藝術領域進行對比和參照的時候,唯獨書法沒有對應,也許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正因為這樣,中國書法才得以按照傳統的形式向前發展,承載著中國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淀。
英國當代藝術史家巴克森德爾在談到歐美藝術史研究現狀時曾對中國書法的獨特性做出過這樣的評價:“我向來歆慕中國,尤其是歆慕她的書法傳統。這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中很明顯的一個原因是:這個傳統賦予了中國文化一種深刻的特質,我愿稱之為一種介于人人都具備的言語與視覺文化之間的‘中介語匯’。甚至通過譯文,我們西方藝術史家依然能夠體會到中國的古典藝術批評縝密細膩、平穩連貫,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這種‘中介語匯’的存在。相比之下,在西方……我們沒有這種‘中介語匯’,我們缺乏一個語言與視覺藝術在其中可以共存的有機統一的思維模式。”[18]這種“中介語匯”就是書法在表達語言、語意的同時,通過毛筆書寫完成了文化與藝術的完美結合,因其深厚的傳統與審美的普及又具有了強大的生命力。所以,作為當代人,我們要擔當起書法藝術在我們這一代怎么樣傳承與發展的重任,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高潮推波助瀾。最終,用漢字思維、漢字書寫思維、書法的審美思維等無形力量去影響世界。
注釋:
[1] 謝貴安《饒宗頤對史學正統論研究的學術貢獻———〈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發微》載《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頁。按,饒宗頤對史學正統觀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其1977年發表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文(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對此一關鍵問題進行了長達五年的準備及研究,系統、全面和深入探討了中國史學上之正統理論。饒宗頤也清楚地道明:“中國史學觀念,表現于史學之上,以‘正統’之論點,歷代討論,最為熱烈。”
[2]《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第2頁。
[3]《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第209頁。
[4]《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第512、513頁。
[5] 參見叢文俊《中國書法史?總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頁。
[6]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三十四《王無競題名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 元?王惲《秋澗集》卷四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歷代書法論文選》,第408頁。
[9] 參見方波《宋元明時期“崇王”觀念研究》一書中“書法中一線單傳觀念的嬗變與流派意識的產生”一章的列舉和研究,南方出版社,2009年,第177—197頁。
[10] 饒宗頤《中國古史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78頁。
[11] 米芾《書史》,載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第974-975頁。
[12]《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04頁。
[13] 叢文俊《中國書法史?總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頁。
[14]《歷代書法論文選》,第715頁。
[15] E-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頁。
[16]《中國書法》2009年第8期,第25頁。
[17]《中國書法》,2011年第9期,第39頁。
[18] 巴克森德爾《意圖的模式》,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168頁。
作者簡歷:
李慧斌,男,1977年12月生于吉林柳河。吉林大學歷史學書法方向博士、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學博士后,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訪問學者。現執教于青島農業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職稱。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書法研究側重于宋代書法文獻與書法史以及書法教育方面,出版學術專著《宋代制度視閾中的書法史研究》一部(南方出版社,2011年11月)。有三十多篇學術論文在《中國書法》、《書法研究》、《書法》、《書法叢刊》、《中國美術研究》、《美術觀察》等刊物上發表。此外,又有多篇論文獲獎,主要有:2007年《宋代制度史層面的書法史研究》獲“全國第七屆書學討論會”二等獎,同年,獲山東省書法家協會授予的“書法研究成果獎”;2009年《從補史到新證——唐宋“院體”書法研究》獲“全國第八屆書學討論會”二等獎。另外,還主持一項中國書法家協會的“2008—2009年度學術研究課題”。多次受邀參加國內重要的書法學術會議,并作主題發言。書法創作以楷、隸、行草和大字榜書為主,作品多次在省級書展中獲獎或入選,另有多幅作品在書法及美術類期刊上發表并作專題介紹。